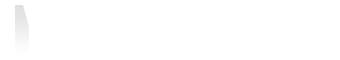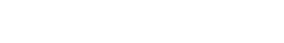在那遥远的地方
发布时间:2023-02-13 10:06:03|
刘三姐,在那遥远的地方 李朝元
音乐对于每个人绝不是可有可无。或许你会反对,说你从来不唱歌,从来不听歌,也从来不感兴趣。是的,你说的没错。起初我也是这样想。我是一个典型的歌盲,音乐对我而言形同陌路。然而对于这一切的改变是在二十多年前: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坐在公交车上,去往旅游的景点,大陆的港台的,华语的英语的,民族的流行的,不管你愿听还是不愿听,它都充斥你的耳朵,震动你的耳膜。熏陶之下,自然也随着流淌过来的乐曲哼上几句。于此说自己对音乐有了兴趣也不尽然。感兴趣的是一次偶然,确切的说是这次偶然后留下的思考。饭局上同事卡啦ok完问我,你最欣赏哪首歌,我不假思索随口而出《刘三姐》。他又问最难忘的是哪一首歌,我也是不假思索的随口而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惊讶于自己的回答。一个歌盲怎么会对《刘三姐》和《在那遥远的地方》感兴趣呢?而且把“欣赏”和“难忘”的概念分得如此清楚,回答得如此确切呢?这是事后的思考,我在寻找答案。音乐是什么?是随便哼出嗓子的几个无词的音符还是心里流淌出来喜悦的心音?还是寄托怀念、追思美好、憧憬未来磅礴于心的波涛?《礼记·乐记》这样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不谋而合,我之所思所想如此亦然。歌盲的我怎么突然间有了对音乐这般深刻的理解?未免看高自己,也未免夸大其词了吧。其实,看高和夸大不是我的主观意愿,如果往深处想,再体会一下生活和音乐,结论自然出来。戴德和戴圣叔侄编著《礼记·乐记》时,“音起于心,感物而动。”也不是随口而出,凭空想象出来的。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原始歌声的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歌声和乐器组合而成音乐,是劳动和生活使然,戴德和戴圣叔侄只是总结和概括生活而已。这样说来我对于音乐的理解,对于音乐的思考也就谈不上“看高自己夸大其词”了。
那么,我生活使然的音乐之根在哪? 桂西北有个宜山县,宜山县有个流河乡,一条清冽洌、翠竹掩映的小河绕村而过,这条河叫下枧河,传说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而我的故乡是宜山县龙头乡,与刘三姐同属一个县,算是同乡。老乡问:“你和刘三姐是老乡?”未等我回答他又说:“你的山歌一定唱得很好听!”我惊讶于这位老乡的赞扬。那是1976年的一个夏天,我正在知青院子里配合生产队这位老乡做木工活。他好像在等待我的回答。回答什么?我自然答不上来。自小在故乡长大,山瑶木洞,穷山恶水,既无学识又无见识,就说电灯吧,九岁那年爷爷领着我和我的一个表哥徒步走了百余里到了县城才见得电灯。至于说“刘三姐”只是听说,未看过电影,也没有听过她的山歌,更不会唱她的山歌;不会刘三姐的山歌也就罢了,或可因为年代久远,或可因为它是一个传说,但是说我从来没听过故乡人唱山歌,连我都不信。二十多年后《刘三姐》再度流行,我打电话问舅舅,舅舅说那时候搞文革、除四旧,山歌被当作四旧铲除,你哪里听得到。我再问“刘三姐”是流河乡的?舅舅说,原来叫流河乡,现在改名叫刘三姐乡。故乡有个歌仙却入目而不识,故乡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却充耳而不闻。我配做故乡的游子吗?从那时起,家里的磁带、影碟、mp3只要与“刘三姐”有关的影视、歌曲我尽将它收藏起来。“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竹子当收你不收,笋子当留你不留,绣球当捡你不捡,空留两手捡忧愁。连就连,我俩结交订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不但倾情于主人翁缠绵悱恻的爱情,更在于它引领我进入青春期的那段暗恋,勾起我无尽的回味和愉悦和享受。我便这样心随歌舞,思随曲动。这便是“音起于心,感物而动”最好的全释。不过,恕我愚钝,借彼而歌,是借了三姐的嘴,借了乔(羽)老爷和雷(振邦)先生的词曲击节踏歌灯火阑珊罢了。
最难忘的歌呢? 要说最难忘的歌先说最难忘的人吧!师姐姓穆,师哥姓许,比我高一年级,都毕业于部队一所中学,同一天下乡,分在同一个生产大队。下乡生活继承了父母部队的优良传统,部队在每个知青点都派有一位指导员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记得下乡的第二天就开始写红色家书,写完要交给指导员看,写得好的“范文”要在知青会上宣读。同样,家里回信时指导员也要选好的 “范文”来宣读。后来又在我们知青小院的屋山墙上建起黑板报,在知青屋里建起“心得体会”栏,每个知青都将自己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写在上边,写得好的“范文”也会在知青会上宣读。知青会几乎天天开,吃过晚饭,掌灯时分知青们陆陆续续走到一起便是“会”。记得,那天是许哥首先“发难”,要师姐朗诵她写在“心得体会”栏的“范文”,师姐落落大方,从炕沿落脚站起,走到大家面前,两条齐肩小辫来回摆,宽松肥大的军裤将一袭短袖T恤衫扎进裤腰,优美的身段起伏跌宕,像电影“女篮五号”里的女主角秦怡。随即,诗一般的“范文”从她的皓齿红唇间飞将出来:踏着晨露,吮吸着麦苗的芬芳,一任春风吹拂我的脸庞,飘扬我的秀发,还有暖暖的阳光,还有暖暖的青春的心房,锦绣的田畴阿,假如春雨为我媒妁,我愿作您的新娘……亦舞亦歌、亦诗亦画。记得师姐读到“还有暖暖的青春的心房”时是用了手掌抚在她的心房那里,然后再将那只唐婉一样的红酥手,展开手掌“请”过我身边的许哥,继续朗诵:“我愿作您的新娘”。知青们热血沸腾,遐想无限。现场欢呼一片,雀跃一片,掌声一片。许哥喊:“穆xx唱一个!穆xx唱一个!”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师姐毫无怯意,问大家:“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心爱的土琵琶!”“唱一首山西好风光!”“唱一首南飞的大雁吧!”“不行不行,唱一首遥远的地方!”还是许哥的喊声。师姐刚唱两句,另一位师哥忙喊打住,说:“让许xx拉小提琴伴奏。”坐在我身边的许哥从炕上拿过自己的小提琴走到师姐身边,将下巴压住琴托,右手的弓弦来回试了几下,看一眼师姐,说:“开始。”“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流浪在草原跟她去牧羊……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师姐一边唱,一边用她脉脉含情的眼睛看着许哥。炕上那位师哥又喊:“许xx你愿她的皮鞭打在你身上吗?”许哥只是瞟了一眼师姐,没说话。却炕台里边的那位师哥按捺不住高喊一声:“我愿意!”激昂的情歌飞出知青小屋,回荡在傍晚的天空。难忘今宵,难忘此情,难忘此景。师姐嘹亮的歌声和她优美的身姿和着许哥悠扬的琴声深深印进我的脑海,此生挥之不去。后来公社组织文艺队,师姐和许哥都被抽了去。在一个节日的舞台上我又看到他们两人配唱的身影。萌动的青春在知青的岁月里勃发,初开的情窦在那个美好的年代绽放。虽然劳动辛苦,虽然生活乏味,但青春美好,情感美妙。那天,生产队割麦子,我和许哥一人一拢,我说许哥你的小提琴拉的真好,他说是吗?我说穆姐的歌也唱得很好,他说是吗?然后低着头挥起镰刀,不一会,将我远远甩在后边,然后再回过头来帮我割去半拢。我猜想许哥一定有着重重的心事,是想念知青屋里的那个傍晚?还是想念那根“皮鞭”?还是想念那个节日的舞台?那次走在县城拉化肥的路上,我给许哥说:“在那遥远的地方”真好听,我都学会了,他说别说了快推车吧,然后他加快脚步,我一路小跑跟在后边。 后来,我们分批分期招工到了不同的地方。记得师姐分配到鲁北一座城市蹲了机关,许哥去了一座工厂,我则分配到一家施工单位,我的单位是流动的,建好了就走,和师哥师姐也没有书信往来和其它联系。所以,不知道他们是否恋过、爱过,惦记过、牵挂过,或许什么都没有,或许什么都有,只在他们心中,在他们的青春岁月和美妙的歌声中,还在只有他们才能读懂的每一个眼神里。工作之后,看过很多演出,听过很多歌曲,当舞台上的歌手站定,悠扬的音乐响起,师姐和师哥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眼前,出现在脑海里,此时舞台上的歌手和乐手仿佛变成师姐和师哥。而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从我的心底飞翔出来,一阵高过一阵,将眼前的音乐覆盖,将眼前的场景覆盖,将眼前的歌手和乐手覆盖。然后在心里不断地问:师姐、师哥,你们还好吗?你们走到一起了吗? “还有暖暖的阳光,还有暖暖的青春的心房,锦绣的田畴阿,假如春雨为我媒妁,我愿作您的新娘。” 我默默背诵着师姐的范文。 我们曾经美妙的青春!师姐曾经嘹亮的歌声!此生不知道是否还可以听她高歌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否还能看见她美如秦怡的身影。 于是,只能打开音乐,传来的是霍思燕“在那遥远的地方”。虽然悠扬,虽然缠绵,却隔离了知青小屋和一屋子的青春和青春的梦想。且闭上眼,借她充一次师姐的歌声,让这首旷世的歌曲在只属于我的夜空,只属于我的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里回荡;在我已即老去的岁月里回荡!久久回荡! 二十多年后偶遇当年知青,他和师姐同在一个机关里工作,我问他师姐的故事,他说没有,她不是许哥的新娘。 暖暖的师姐青春的心房,您做了谁的新娘? 我想许哥一定在思念,一直在思念:在那不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散文编辑:江南风) |
 |
祖居 | 21-05-30 |
 |
心 声 | 21-05-30 |
 |
香港爱的短篇 C33(孙恩立) | 21-05-30 |
 |
解读(十四) | 21-05-30 |
 |
潘玮柏马来西亚演唱会宣布延期 详细时间 | 21-05-10 |
 |
解读(五) | 21-05-30 |
 |
蹲在贤臣河村落外的老屋 | 21-05-30 |
 |
怨 | 21-05-30 |